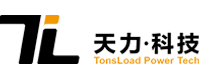推开窗,晨雾里飘来楼下早餐铺的豆浆香。2026年的第一缕阳光正轻轻落在阳台上,叶片上的水珠折射出细碎的光。这一刻,我突然想起去年今日,也是在同样的晨光里,我看着朝阳,许愿要成为更加勇敢自由的人——如今站在岁末回望,那些关于“勇敢”的答案,早已藏在了生活的褶皱里。
2025年的春天,我坐上了去往青岛的列车,窗外的原野正被春风染绿,而我的心,正奔赴一场与三年前未竟梦想的温柔重逢。当列车缓缓停驻,我站在熟悉的校园里,踩着满地梧桐落影,终于走进了这三年来魂牵梦萦的青园。那一刻,我仿佛看见三年前那个跌倒在人生岔路口的自己——她眼中闪着未灭的星火,却因外界的风雨而瑟缩。而此刻,我轻轻执起她的手,与她温柔相拥。那些曾如霜刃般割心的质疑——“女生读那么多书没用”“你都快三十了,还读书干啥”——如今再想起,竟连回望的力气都省了,只化作春日里微不足道的尘埃。我忽然懂了,所谓勇敢,从来不是与喧嚣争辩,而是学会在风雨中捂住耳朵,只听自己心跳的声音。当梦想终于在指尖绽放成花,当登顶的晨曦照亮所有跋涉的脚印,那些曾经刺耳的议论,早已在时光里蒸腾成雾,连痕迹都寻不见了。
此刻的校园,樱花正沿着青瓦白墙攀爬,风里飘着墨香与新叶的清甜。我伸手触碰墙上的爬山虎,触到的是岁月里最坚韧的温柔——原来最动人的风景,从来不是站在顶峰俯瞰众生,而是终于能与过去的自己握手言和,然后笑着说:“你看,我走到了。”
蝉鸣撕开夏夜的帷幕时,我正攥着好不容易抢到的凤凰传奇演唱会门票,开车走在通往青岛的高速上,这是属于我的“极限挑战”——单休日往返两城。演唱会开场前,我站在馆内,看着热闹的人群,听着蝉鸣与远处海浪声在夜风中交织。当灯光暗下,《奢香夫人》的前奏响起时,我忽然与世界失联了三个小时——手机信号在喧嚣中沉没,人群的呐喊声浪托起了我,让我回到十岁那年,蹲在老电视机前跟着“乌蒙山连着山外山”手舞足蹈的夏日。我为他们呐喊,喊到喉咙沙哑也浑然不觉。当玲花和曾毅最后谢幕时,全场荧光棒海掀起最亮的一波浪潮。后来我才知道,凤凰传奇因档期调整,演唱会突遭中止,而我看的那场竟成了2025年收官之作。蝉鸣还在耳畔,可此刻的寂静比任何时候都清晰。我想起自己为了这场演唱会,如何算着我的时间,如何在地铁上补妆,如何在进场前反复确认门票——原来所谓勇敢,从不是等待万事俱备的从容,而是看见星火便奋不顾身扑向光的冲动。
原来所谓“跟世界失联的三个小时”,不是逃离,而是与最本真的自己相遇。而所谓勇敢,就是当蝉鸣最盛时,说走就走;当星光最亮时,说爱就爱;当终点突然降临时,还能笑着说:“我来了,我看见了,我无悔了。”
秋深时,我收到了朋友从西北寄来的胡杨叶书签。那是她蹲在沙漠里一片一片捡的,每片叶子都写着一句她想对我说的话。她终于到了民勤,和仲麟一起种下了梭梭树。那时候我明白,勇敢不是与生俱来的铠甲,而是明知沙粒会割伤手指,仍要蹲下身把树苗埋进风的漩涡;是清楚沙漠会吞没脚印,仍要在日落前数清最后一株幼苗的呼吸;是当所有人都说"民勤终会消失"时,偏要相信沙地上能长出永不褪色的春天。后来我常想,那些被她写满句子的胡杨叶,哪一片最勇敢?是写"风可以吹散头发,吹不散决心"的那片,还是写"种树不是对抗沙漠,是学会与风沙共舞"的那片?直到某天我翻到夹在书里的最后一片叶子,背面用铅笔浅浅写着:"所谓勇敢,是看见荒漠时,先想起种树的人,而不是逃跑的人。"
此刻窗外的银杏正簌簌落下,我忽然懂了——勇敢从来不是瞬间的壮举,而是像梭梭树的根须,在无人问津的岁月里,默然扎进更深的土层。它藏在朋友磨破的登山靴里,在民勤人晒得黝黑的脖颈上,在每片被风吻过的胡杨叶的褶皱里,更在那些看似重复却永不放弃的清晨与黄昏。
窗外的阳光渐渐爬上了书桌,照在2025年的日记本上。最后一页写着:“所谓来日方长,不过是在每个今天里,认真活着,温柔待人。”最好的时光,从来不是未来,而是此刻,是手边的这杯热茶,是窗外的这缕阳光,是身边这些让我愿意温柔以待的人。
管理部 毕文馨